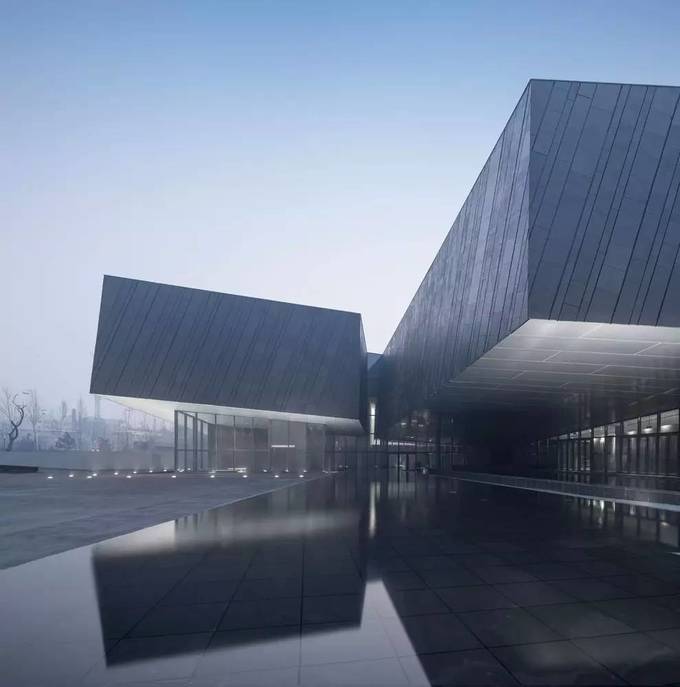【艾景奖现场】2018第八届艾景奖巅峰对话——未来乡村
12月2日下午,2018第八届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会暨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风景园林委员会学术年会议程来到巅峰对话环节,由东方易地总裁兼首席设计师李建伟主持,对话嘉宾有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局长龚建阳,北京观筑景观规划设计院首席设计师孔祥伟,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主任、教授成玉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风景园林学科带头人刘晖女士,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景观学院院长詹姆斯·希契莫夫,新加坡Tierra景观事务所设计总监梁达民,荷兰MLA+建筑规划事务所设计总监马库斯·阿彭泽勒,安娜·卡特里娜。

李建伟:有请几位对话的嘉宾,首先是詹姆斯·希契莫夫先生、新加坡Tierra景观事务所设计总监 梁达民、荷兰MLA+建筑规划事务所设计总监 马库斯·阿彭泽勒先生,Founder of LWCircus-Onlus organization 安娜·卡特蕾娜,北京观筑景观规划设计院首席设计师 孔祥伟、福建农林大学园林学院院长 董建文,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系主任 成玉宁。
首先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孔祥伟:大家下午好,上午论坛介绍过了,这几年主要做乡村的营造设计,也做了一系列的乡村,从总体营造的角度,未来乡村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所从事的主要还是从设计角度解决一些问题,非常开心跟大家交流。
梁达民:我非常项目中国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组织谈乡村的未来,你要知道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谈这个问题,但是新加坡没有乡村可谈,在马来西亚要谈到这样的课题,需要牵涉到很多城市上、管理上、政治、经济上问题,所以我非常羡慕你们。
马库斯:大家好,我是荷兰MLA+建筑规划事务所设计总监 马库斯·阿彭泽勒。
詹姆斯:怎么管理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场地,尤其在乡村地区的景观,仅仅靠设计是不行的,我们真正重要的是对进行长期的管理和治理,怎么样更好对乡村进行管理,在这个方面特别重要,怎么样跟本地人进行互动和对话,跟他们交流,怎么样把一切整合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议题,这也是我感兴趣的。
安娜·卡特蕾娜:大家好,我是安娜,我来自意大利,我也是一个景观园林设计师,我是在斯洛文尼亚出生,同时我也是NGO的创始人,我们应用设计和社会实践致力于乡村地区的改善,50年前在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小村落,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小村落身份感和特色很重要,现在当我们在不断全球化,怎么样保留当地的风貌特色,自己的特色很重要,保护我们的身份,保留我们对这个地方对过去的记忆很重要。因为这其实是特别珍惜珍贵的,也是对我们未来特别重要的,谢谢。
成玉宁:各位好,我是来自东南大学的成玉宁,超过一天半的时间,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乡村振兴与发展必须基于对土地与历史的尊重,需要智慧的规划和智慧的设计,更需要智慧的营造,写不是小聪明。
董建文: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农林大学农林学院的董建文,非常荣幸坐在这里跟大家交流,福建农林大学在福建园林景观系统内我们是做了一些贡献的,在我们福建省省内大多数从事风景园林景观方面的人士很多都是我们的校友,所以我们这两年有一些进步,我感谢大家的关心,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关心我们学校,谢谢大家。
刘晖:我主要负责风景园林学科建设,感兴趣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来自于本土风景园林历史和理论,更多就是昨天也讲过,地景文化产生于中国传统文明体系中,对自然环境的认知以及最后形成形胜和一种风营建的思想和智慧。第二个研究方向,好象不是我这个学科,但是非常感兴趣城市建成里面的环境生态,更多是植物群落中如何介入到其中营造城市适宜的生物多样性。第三个研究是西安城市形态的演进,我很希望能找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表象合理象在促进城市的发展。很多人在研究历史理的时候,不面对历史就无法面临未来。乡村是我在最开始做小流域的时候,在黄土高原走过十天时间,让我彻底了解了什么是乡村。原来只是玩过或远远看过,但是做了四年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之后,看到了乡村生活和乡村跟人的关系,但是现在很害怕触碰乡村,我觉得乡村是非常复杂而敏感的东西,但是我很希望能够关注身边,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乡村问题。
李建伟:我收到非常有趣的问题,外国乡村未来发展有何借鉴意义,他们走过的路对中国有什么借鉴?可以在一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安娜·卡特蕾娜:乡村修复很重要,我们不太做重建,不管是房屋还是村庄希望可以保持下来,在这里我特别开心,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同行的分享,比如说世界人居和中国,如果有这么多平台讲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詹姆斯:詹姆斯:我们也尽量保存景观和人文的遗产,所以我们在做项目过程中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我们希望不用破坏村庄和景观,在我们规划中其实是有一个保护区,每次村庄都会有保护区,假如村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遗产我们就会划为保护区。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如果用彩色的颜料涂抹墙或做门,这些是可以的,但如果是保护区,当地农民是不允许这么做的。村民很多是住在保护区里面的,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对于当地的文化保护非常重视,他们对于居住的房屋是不能做太多改变的,但是他们仍然愿意住在这个地方。
马库斯: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但是不能复制。因为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当地文化,假如就是复制一个概念,把重建的概念、振兴概念复制出来的话,其实就是摧毁了当地的问题。当你看乡村的时候,如果一个地区一定把当地的文化研究清楚,很多乡村就算隔的地方不是特别远,但文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不要觉得旅游业就是最终的解决方法或者觉得他是经济大法,它可以为某一些村庄带来未来,但不是唯一一个驱动力。我们开一些城市博物馆,或乡村博物馆,或者是让大家种植苹果和采摘,但是会让城里人觉得现在是体验了乡村的生活,这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想说旅游业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不是把一个乡村变成了旅游热点就可以恩变成未来乡村。另外一个是规划体系,以前做了很多大型的规划,在过去三十年很多城市发展都是做大规划,但是我们可以把规模进一步缩小,可以用同样城市规划的发展思路做,但是不能完全放在一个农村中,我觉得农村的重建应该是从当地开始做小的规划。我是完全同意的。
詹姆斯:中央化规划的体现出当地文化的多样性是非常困难的,可能你们会觉得城市规划做得挺不错的,城市有很多多样化,但可能从外人眼光觉得城市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需要分体化、去中心化、分层次的规划方式。
梁达民:我可以从新加坡的点说一下,虽然我是华人,但也是新加坡人。我知道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包括马来西亚也是这样的,我想要说的是就算是在英国殖民时期,也是想要确保不同的种族是和平相处得,假如你在新加坡会看到有一些印度、华人或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遗产,当时英国人就希望种族间可以和平相处,后来新加坡成立以后,新加坡政府也是希望所有民族都可以和谐相处,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几句话就可以总结出来,假如你可以作为学者或游客来到新加坡,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李建伟:感谢各位嘉宾的回答,这里有一个问题请成玉宁教授回答,就是现在中国农村的现状是大批劳动力流失,农村再好的规划也没有人去实现,怎么样谈乡村振兴?
成玉宁:这个问题是不是来自农村的朋友提的,或者是真的关心农村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命题不是伪命题,景观是农村生活自然而然的显现,当农村存在空心村,劳动力流失,当农村土地结构产生流转的时候,这时候谈景观,我觉得意义不大。唐先生说的问题更是切下当下农村的现象,但是我相信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特色不是简单借鉴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哪一个片区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包括城市中间再次出现劳动力回流,有一批劳动力回到农村,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引起的。在这个亲前提下,我觉得中国农村一定是跟西方农村不一样的,我们农村土地资源有限,我们土地生产力有限,当土地、景观与土地效能挂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的景观不是狭义的景观,而是真正的景观,不是所谓的人造景观。
举个例子,刚才四位外国朋友都说了欧洲景观给中间的借鉴,我举个欧洲景观的例子,试图以这个例子间接回会刚才的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最富裕国家瑞士,瑞士曾经这个国家也改变土地结构变成梯田生产粮食,本来长草长玉米的地方,结果被种麦子了。所以种麦子一定需要更多的水,因此自然地形改变了,变成梯田,中国和中国一样的梯田。30年过去了,瑞士人发现长出来的粮食是有的,但是改变了环境的代价是巨大的。近30年,包括十年前到瑞士,我看到一个环境修复计划,就是把土地修复到最适宜他的生产方式,所以又是种草,把原来人工沟渠恢复成自然的状态,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给中国的启示,也就是间接回答刚才唐先生提的问题,当我们的土地有一批劳动力回到中国土地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将劳力和土地资源结合在一起,通过资源的结合最终离不开对土地自然规律的尊重,所以中国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过程。当劳动力跟土地结合在一起,当生活资料和生活方式有机统一,我想中国未来乡村景观是可持续的。
李建伟: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是非常具体的,我想问问孔祥伟,你是做了很多具体的乡建项目,一个是投资方和建设方对项目思路的干预性非常大,对设计项目的落实又不强,都在谈思路,但是让你项目很难落地,主观过程很难把控。施工方从施工利益考虑,怎么样使项目最终能够实现目标。
孔祥伟:三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投资方对于项目的干预问题。当然我是常年在一线做具体的设计,对我来讲,每一个项目都是具有个体性的,不具有普遍性的。五年过程中,可能最开始第一个村子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不同方面的干扰,但我觉得干扰主要是来自于政府官员的干扰,我很多项目与合作方耦合度非常高,有非常一致的目标。在最早的时候,我所说的是从政府的角度干预,干预你开发强度的问题、关于设计风格问题,这的确是很困难的。牵涉到保留与保护,新建的设施或建筑和景观的风格问题会出现矛盾,当然从设计师来讲,一直是要坚持,坚持到最后项目落成,你就能够获得成功,慢慢后来在项目中,干预从我个人体验角度,因为这只能讲我个体的经验,不是共同的经验,干预会越来越少,我所有的合作伙伴,包括后来又很多政府委托都非常尊重设计思路和设计意图。当然这中间需要斗争,每一个项目都是一场斗争。
第二个问题关于施工方问题,就是施工质量的把控,这确实也是一个事问题,因为很多项目都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施工保障也很不好,有些施工没有场地,这就需要设计师从在场营造的角度参与施工设计。我记得做第一个项目的时候非常执着,比如在乡村施工方做出来时候,跟效果有差异就拆掉,现在慢慢拆掉的东西越来越少。当你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施工不近如意时候要改变思路,大家都知道,陶瓷在烧制过程中会发生窑变,这反而是另外一种美,所以过程中你自己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但是更多是要跟工匠紧密结合,跟工匠深入交流。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现在很多乡村中的项目,投入很大,回收期很漫长,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包括有些民宿、旅游投入进去后,可能是五年十年把建设成本持平都非常好了,但是我总是客观辩证看待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目前的乡村一旦走过之后,五年时间走过500多个村落,每年大概有100多个,你就会觉得这里有资本的力量,哪怕是一个民宿主或小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经营者一旦到达了村子,开端就是好的,总是会改变乡村,更不用说很多大资本大产业进入乡村,从我这个角度讲是积极的。当然设计师一定要很好的选址,譬如一个村子,有些区域是保护的,刚才詹姆斯院长讲的,我们会在风貌特别好的地方保留,在残破风貌一般的进行改造,中国很多乡村是演变过程,传统的古村落,实际上在我走过的这些村子占的很少,大概10%不到,大部分是一般的村子。我们很好的选址,当然作为设计师是反对跨界的,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专业跟其他一系列专业的融合,比如说跟经营策划的融合、最终运营融合、跟当地农民融合,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放弃和丧失自己的专业所在。最大的作用还是发挥自己的能量,从整村的角度营造一个全新乡村环境,这个环境从自资源体系到田园再到村庄,再到景观,创造出好的产品,以对抗以解决经营和可持续风险,这是设计师所能做到的。
我的回答到此结束,谢谢。
李建伟:面对乡村现状,做乡村规划的时候,如何避免乡村建设项目的同质性和均质性。
刘晖:在我认识到的乡村,中国乡村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家盖的房子,大家都会跟着学,实际上不是设计师设计的,如果自己家盖的房子不错,反而大家都会学,乡村就是喜欢跟风,这可能是历史以来在传统村落中,村庄里面反而是大家互相学习的,没有建筑师设计的的,避免同质性,是跟土地本来的肌理要结合在一起,并不在于这个房子和那个子不一样,更应该看到这个村庄整个肌理和整个土地环境之间的关系,关中的房子就不应该跟南方的房子一样,关中种的树也不应该跟南方的树一样,这在总体规划中应该理解。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了乡村规划,我觉得我是不敢碰乡村的,因为做乡村一定得去乡村,你得跟村支书和所有住在乡村的人对话,你才能做乡村。如果不懂乡村的时候,要碰起来是会毁掉乡村的。
均质性的提法,我觉得要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事情,包括现在有一个命题就是千城一面的概念,我觉得在古代城市中就是一样的,只是在整个城市选址和整个大格局中是不一样的,我看到有时候古代城市照片的街道和那个街道真得很像,没有说完全不一样,反而现在很多为了不一样排名不一样,反而是是有问题。我倒是觉得村庄选址和整体结构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很重要。
一个村子一定有主力面,比如村口,国外就有教堂,从村口是村子最有特点的画面,我们应该保护这个东西呈现在人们面前。像袁家村的发展,最后就失控了。我们应该对所有村落,包括田园都应该做景观的评估,但是什么是最好的,特点在哪里。首先要将特点和特色,所有用一个乡村景观一套方法评价,然后再去看怎么做这个规划。
李建伟:下一个问题就给董教授,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文化有地域性,同时文化也有纵深历史连续性,这两个方面如何影响乡村建设?
董建文:就文化来说,我本人文化并不深,好象谈起来不合适。但由于我来自农村,也在农林大学,可能对农业农村有自己看法。感觉这个问题乡村规划过程中一直要思考的问题,有什么文化特色,有什么历史,我感觉有点像刘晖老师讲的部分内容。现在很多人很多团队做乡村规划,我也觉得有的团队并不适合,因为对农村事情并不了解。包括现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既然是一个战略,就是一个长期的东西,而不是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的东西,一个规划团队在不了解乡村文化的时候,你冒然进去就会出现像成玉年景老实说的祸害乡村,我个人觉得对乡村文化的理解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乡村特色的提炼,不是说作为一个规划师拿来植入的,我反对一些用词,而是要激活,包括梳理出一些东西,将乡村中的文化梳理出来。我们的乡村,尤其像福建很多乡村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形成了很多独特的东西,你怎么梳理出来,这应该是规划师们要关注的东西。
另外,这个问题也泛,我顺便想把对乡村规划的思路简单说一下。我刚才提了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战略,不是一天两天的。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做的事情也不应该是短视的,包括有些用力不要那么猛,速度不要那么快,干预不要那么多,包括设计师对乡村的干预,如果你对乡村干预那么多,很多文化就被你无形中侵犯了,被你植入了。对于文化,对于乡村规划,从历史渊源也好,从文化特色也好,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要认真的梳理,这是我对乡村文化的理解。
李建伟:关于农业的面源污染在中国非常严重,因为我们要保证农业的丰收应用了很多化肥,农业的污染已经成了对国家土地安全的威胁,想问一下来自四位来自于国外的嘉宾,有没有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治理农业的面源污染。
詹姆斯:必须要有强力监管措施的监管框架,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中国就直接用杀虫剂或化肥,完全不顾任何法律法规,就直接喷洒农药。我觉得这其实是不可持续的模式。特别是小农发展上,因为没有监管,没有控制,所以这种更加肆虐。欧洲会尽量用同样的统一,比如欧洲的农业通常都是有一些保护措施,在上面不可以随便喷洒东西,还有一些水稻是不可以触碰的。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有更加严格的监管,现在来说,监管和欧洲来相比有比较宽松,比如在欧洲某些地方是不可以喷洒农药不可以喷洒灭虫剂,实际上政府和农业从业者签署了条约。
另外一点,我们尽量做一些有机种植。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说从生态角度会发现英国如果想做有机是需要一体化有机,有些地方是完全要做有机的,甚至为了生态连有机种植都不可以做。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想要取得经济发展和生态间的平衡就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可以看一下,欧洲有些国家愿意为有机产品而付出更高的价钱,当然他们也是比较有钱。还有一些人因为本身种植成本比较高,的确愿意花这部分钱保护环境。
安娜·卡特蕾娜:我觉得很难相比,因为我们国家和你们国家不一样,所有这些国家都会有一些不允许使用的塑料,因为现在海洋已经到处都是塑料了,越是用塑料,在海洋中就会有越多的塑料。在意大利是尽量做有机农业,我们希望可以更多关心农村。说回农村,我们希望可以用一些传统的方式进行种植,比如说在一些农村里面可以应用一些想法,让更多人可以重新回到农村,这是简单而传统的方式,我们想要达成就是可持续发展。有些时候我们会说进步也是一种退步,因为进步的话就会创造出很多污染,也会使整个星球受到污染,而且使整个生活退化。我们可以想想,能不能用一些传统的方式做奶酪或传统方式养牲畜,就是用比较小农的方式,用传统的方式慢慢进行生产,但是对于我们地球来说是可持续发展的。每一次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像这种小农经济生活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可以告诉下一代怎么做传统的东西,告诉他们一些传统的智慧。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传递文化中,这样一种小农生产方式都可以给下一代带来很多得好处。
马库斯:我觉得我们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思考食物,像土地污染的问题,我说一下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尽量的不去污染土壤,不用杀虫剂污染土壤,比如像在荷兰有一些工业化的食物生产方式,他们尽量不使用杀虫剂,因为他们会控制环境,让环境更好一些,就不需要使用杀虫剂,还有土壤的营养剂,如果土壤保护得好,你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们现在可以用技术改变原先的传统施肥方式,我觉得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再说回来,我们也可以走回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会更多的尊重土地、气侯等等,把新的技术和传统方式结合起来,就可以有更多的产量。我觉得技术还是重要的,因为农业很多人觉得是低技术水平的活,但其实并不是如此。
另外一点,对于乡村来讲,现在一直把技术的理念局限在城市里面,觉得只有城市需要这个机械化,需要技术,但是我觉得农村乡村也是需要科技的。这样也可以使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少。有了更好的农业技术,就有更多的可能性,让农村的人赚更多的钱,所以我觉得这两者都是可以结合起来一起解决的。
梁达民:我把这个话题改成污染吧,一个小岛因为需要水所以新加坡的水从厕所排出来的水是绝对不能进入水沟的,这是很重要的话题。即使你那栋楼是靠近河,你的水也可能去多几公里以外的污水处理厂,如果你从经济角度是浪费钱,但是从一个整体经济角度说,如果河水带给我们好的环境,那河水旁边的地价和周边的环境就直接上升了,这盘旗要看大一点。谈到农药问题,如果把旗看得太小,你会觉得是亏本生意,但如果把旗看大一点,可能这不算是亏本生意。